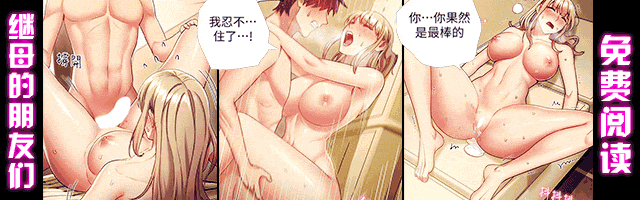06-灰幕之下
朱国的铁壁倒下,沙民成为替罪羊。眼前一片混乱,愤怒和痛苦几乎凝结成实体。
楚云飞脑中浮现战乱时河流染红的场景,看着那支箭的来向,双眼充血,几乎就要跃出窗外。
裴君玉深知楚云飞性格,一手飞快勒住他的腰,一手摀住他的嘴,低声道:“云飞,忍着点。”
裴君玉的力气对楚云飞来说不值一提,随手一挥就能挣脱。但以前两人经历过无数危难时刻,紧密相依,裴君玉的手和声音,对楚云飞而言,有不可思议的安定效果。
裴君玉在他耳边小声说话,声线平静:
“他们的人自会过去,靖王亲兵训练有素,该找到就会找到,不该找到,就不会。”
如果是后者,“找不到”本身就是一项警讯。目前两人的立场尴尬,一出现便会坐实刺杀的罪名,只能等待。
“先别急,我们的线索还不够。幕后的人既然亮了刀,人迟早会出现,到时再出去不迟。”
听着裴君玉冷静的声音,楚云飞呼吸逐渐平缓,他闭了闭眼,拉了下对方袖子,示意裴君玉松开。
裴君玉再次看了外头一眼,胸口染血的靖王已经被带走,兵士们正在清场,人民的低语充满怨恨。
他伸手阖上窗,将外头的声音隔绝。
当夜,靖城下起惊人的大雨。
雨声铺天盖地,水像天塌了似的泼下。大滴雨水密集成一片片雨帘,将靖城笼在其中。
楚云飞坐在床边,手虚拢着弯刀。这一切都让他本能的警戒。
他问:“你还不睡?忙了一天,该累了。”
裴君玉躺在床上看他,摇头:“不困。”
裴君玉一下午都在客栈楼下探听消息,和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。他们两个外来人,出外引人侧目,一直窝在房里也惹人怀疑。楚云飞即使变装,没说几句话就容易锋芒外露,能对外周旋,保持安全的人,只有裴君玉。
目前一切还扑朔迷离,王府戒备森严,全城肃杀,全境封锁,两人被困在这里,只能伺机而动。
楚云飞看着窗外,道:“我守夜,你睡吧。我会护着你。”
裴君玉文,楚云飞武。现在,轮到楚云飞了。
来时一路都是杀手,对方早知道他们要到藩地。即使中间都已经处理干净,并且甩掉追踪的眼线,他们的行踪,仍随时可能暴露。尤其,不知得在这儿困多久。
人在敌营,一朝被发现,不只身死,还会殃及边境沙民。
所以,随时都不能放松警戒。
房间只一豆灯光,映出楚云飞挺直的背脊。
裴君玉看着他,沉默半晌,道:“有时,我真希望我会武。”
每次都只能看着对方的背影,被护在身后。他不喜欢这种感觉。
楚云飞转头,认真看着他:“你这样就很好。”
他是真心这么想。裴君玉会的事,他学不来。
虽然练武有天分因素,但只要努力,便能到达一定境界。况且,在战场上,一个强大的人没有太多用处,需要的是强大的兵团。
更重要的,还有谋略以及后援。
即使再强的将军,没有粮草,也只能愤恨而终。
但裴君玉即使身在绝境,也能从容周旋,并且一针见血的分析情况。这不是一般人能学来的。
或许,人总会羡慕别人没有的东西吧。楚云飞想。
裴君玉心知对方不明白自己心思,垂眼一笑:“承蒙赞赏。”
07-暗影之中
楚云飞虽不大明白裴君玉想什么,但他俩认识多年,即使在昏暗房间中,没看清对方表情,光听声音,也知道裴君玉不对劲。
楚云飞正要开口问,却突然一凛。
他无声站起,看着门口的方向。刀缓缓出鞘,在烛光下闪着危险的光芒。
因为,他听见了不该在这时出现的声音。
咚,咚,咚。
非常轻的声音,从走廊远处响起。
这不像脚步声,更像是……拐杖敲击的声音。
但,大深夜的,会是谁?
楚云飞吹熄灯火,房间陷入一片黑暗。
声音移动的速度很快,但每隔几步,便会稍有停顿。
楚云飞耳力和记性都极好,他转头,用唇语说:
──有人在检查每个房间。
发出声音的人,在每个房门前停顿数秒,然后离开。
楚云飞手握在刀上,犹豫不决。裴君玉按住他的手,让出一侧的床。
──睡。
裴君玉无声地说。
楚云飞明白裴君玉的意思。
不清楚来人的底细和目的,且对方还不确定目标在哪,不如先静观其变,装成一般投宿的旅人,在床上装睡。
两人难以出城,现在状况扑朔迷离,裴君玉让他收敛锋芒。
楚云飞干脆地和衣
躺下,但全身仍保持警戒。
对两个成年男子来说,这张床实在太窄。一躺上去,即使楚云飞刻意背对,两人仍肌肤相贴,几乎是互相依偎的姿势。
裴君玉在他耳边用气音道:云飞,放松些。
耳边湿热,不知为何,楚云飞感觉更不放松了。
他拉住裴君玉手背,快速用手指写道:用写的。
对方只停顿几秒便继续走,代表在短时间内,便能确定状况。此时是深夜,房间内多一片昏暗,对方很大可能是依靠耳力。
裴君玉在他背上写:装睡要像一点。
楚云飞:我很安静了。
裴君玉:你太安静,不对。
写毕,他突然探身抱住楚云飞。
突然的肌肤相亲让楚云飞一惊,但他随即强迫自己放松下来。
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在对方的温度、吐息和气味都近在咫尺的状况下。
裴君玉没有熏香,但身上却总是若有似无的,带着兰草的浅淡香气,让人想到春日的原野。
明明是相当温和的气息,此时在黑暗中,却不知为何,强烈到让人无法忽视。
楚云飞强迫自己将心神放在外面的动静,但身后的手却不放过他。
那双手没有做过分的事,理论上。那双纤长的手,只是简简单单的,放在他的胸口。
放在他跳动的心脏前。
裴君玉在他胸口写:你的心跳好快。
楚云飞拉开他的手,对方又不屈不挠的放回去。楚云飞从不会对裴君玉用力,结果就是两人反复数次,简直像打闹或调情,最后手还是厚颜无耻的贴在他胸前。
楚云飞耳朵红了,有点尴尬:做什么?安静点!
裴君玉小声笑:就是不能太安静。
一般人,即使是陷入沉眠,也多少会有些声响。但楚云飞太紧绷也太安静,呼吸规律,一听就是武人,反而会被发现破绽。
在两人打闹中,“咚咚声”已经到了门前。楚云飞呼吸一紧,随即被裴君玉摀住,按在床上挠痒痒。
站在门外的身影停伫。他身形瘦而高,比起人,更像一道鬼影。薄薄的门板后,传来压抑的喘息声,和恼羞成怒的低语。
像是在客栈深夜常见的事。
那人不大想多听,没停伫几秒,便接着往下一间房间前进。
过了一会,楚云飞听到“吱呀”开门声,和轻微的“啪答”击打。没多久,便换成细微的衣物摩娑声,伴随“咚咚”声逐渐远去。
就像是,客栈中有谁被拖走了。
08-舍生取生(1)
四面寂静后,裴君玉和楚云飞对视一秒,同时坐起身。
楚云飞看了一眼窗外,裴君玉知他心思,问:“去看看?我跟你一起。”
楚云飞摇头:“不安全,你待着。”
裴君玉转身走向门口,竟是要自己出去。两人此时一起离开并不安全,这不像裴君玉的作风。
楚云飞不知裴君玉想确认什么,但深知他执拗,无奈点头,道:“我走窗外,如果你被发现──”
裴君玉接口:“就说我是起来倒水的。”
楚云飞:“……你觉得别人会信?”
裴君玉道:“我有办法。”
不多久,某间空房的窗轻轻打开一条缝,接着夜风吹入,楚云飞随之无声跃入房中。
裴君玉已在房内,站在空荡的床边沉思。
楚云飞环顾四周:没有血迹,油灯依然在燃烧,房间整齐干净,完全不像是刚刚经历诡异事件的地方。
裴君玉:“从地面的灰尘来看,人是从床上被拎起,接着放到地上,被拖离房间。这里的木门老旧,边角破损,勾到了他的衣物,留下一丝褐麻。”
楚云飞:“‘他’是谁?”
裴君玉却没回答,而是反问:“云飞,你觉得是谁做的?”
见楚云飞没说话,裴君玉继续道:“你知道做这件事的人是谁。或许,很久以前,你就知道他们。”
楚云飞沉默半晌,道:“君玉,你什么时候知道的?”
裴君玉:“三年前,你死后不久。”
“我一直想知道,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,逼死你的人是谁。”
“在沙民的故事中,无辜的孩子被献祭。他的灵魂在烈火中被淬炼,获得第二次的生命,化为红鸟。”
“云飞,即使我有猜想,还是想当面清楚地问你一次──当年献祭你的人,是谁?”
轻微的“咚咚”声响起,几人一僵。
一名穿着粗布衣的老人,突然出现在厅堂中。他很瘦,瘦得像根枯木。面容平凡,眉间有深深的皱纹,即使不说话,看着也是一副愁苦脸,看着像寻常的乡野老人家。
但往下看,却一点也不寻常。袍子底下,原本应该是脚的地方,只有两根冰冷的铁锥子。
那两根锥子前端尖锐,染着褐色血渍。用它前行时,便会发
出轻微的“咚咚”声。
他缓缓地问:“怎么啦?”
他的声音像拉坏的二胡,嘶哑得令人不适,语气惫懒随意。
厅堂中的数人面容僵硬,领头人行礼,声音干哑:“拜见先生。”
“先生”就是“先生”,监控者,行刑人,没有名字,也不需要名字。
他们这些人,是国家最缜密的天罗地网。
另一头,楚云飞和裴君玉躲在一间已毁坏的庙中。
对方以为他们会马上逃出,他们利用这一点,先躲在客栈地板底,在对方注意力转向外面时,闭气从沟底逃了出去。两人到达庙里时,早已满身臭泥,看着像两个泥怪,狼狈不堪。
倚着破败的神像,两人同时长叹一口气,接着同时相视大笑。一边笑,又因为太臭而不住呛咳。
裴君玉边咳边笑:“今日当了一回沟鼠。”
楚云飞摸着肚子:“倒也不坏,不过沟鼠肚子饿了。”
裴君玉:“嗯,那我们去当米仓里的老鼠。”
他们以前流亡时也常说这种闲话,米仓里的老鼠,便是要钻进别人家白吃的意思了。
楚云飞笑出声,但他笑归笑,神情依然带着警觉,不时注意周遭。
这里还不够安全。
不如说,这座城,恐怕已没有安全之地。
裴君玉也深知如此。他自从看到靖王遇刺,心中便有不祥预感,刚才自觉马上就要到阴曹地府,没想到还能苟活几刻。
常人谓裴三公子淡然自若,进退有度,即使在最危急的状况下也指挥若定。三年前楚云飞死后,这一点越加明显,以往的顽性和玩笑话,也都随着火焰焚烧殆尽,只剩下完美若人偶的裴三公子。
这些,一半是性情使然,一半因为他早已将一切安排好。即使这世界少了他,他的计划依然会运转下去,尽管结尾他不能得知,但也已尽力而为。
他们在长久的流亡之后,带着伤痕和风沙回到朝廷,以为一切已结束,他们打倒一切。但无论当年楚家的灭亡,皇子出逃,一系列事件背后真正的理由,他们从来没有真正了解。
楚云飞平时看着大剌剌,但他作为楚家遗孤,是最先明白的人。接着,在他准备将一切翻出来时,被逼死了。
这些是裴君玉之后才知道的事。
他非常后悔。
所以,他用尽一切对抗。那仁和他性格相左,但在这件事上立场一致。姬无缺则相反,比起对抗,他选择融入其中。
现在唯一的变量,是在计划半途复活的楚云飞。他已经尽力屏除太多情感,将楚云飞安排进去。他作为沙民的信仰和领袖,看似在核心,却游离在核心之外,如果依照计划,一切将安全无虞。
所以,一切理应没有问题,理应。
楚云飞的复活是意外之喜,却也让裴君玉变得无法割舍世间。
他不想死了。
但是,滚轮早已转动,事已至此。如果计划是奔涌的河,他已自己跳入水中。虽能游动,却也受波涛宰制。
何时死,何时生,早已不是自己能控制。
或许,也从来没人能真正控制过。
裴君玉直直看着楚云飞。
在最危急的时候,所有计划、谋略都已从他脑中消失,眼中、心里,只有面前的人。
世人谓裴三公子从容淡定,智谋高超,但他同时也是肉体凡胎,心脏会因为他人而快速跳动。
裴君玉开口,正想说什么,却突然一僵。
楚云飞正专心对付身上的泥,没注意到裴君玉一瞬的怔愣。
裴君玉的失态只有一瞬。他缓缓地眨眼,面上浮现平时的笑意,说:“云飞,你还想吃当年的叫化鸡吗?”
这不是他原本要说的话。
但现在,这些都无所谓了。
09-舍生取生(2)
当年初见时,前将军楚云飞和裴家公子都还年少。和日后的和谐不同,一个觉得对方假风雅,面上笑咪咪地不知在想什么。另一个则觉得对方粗鲁凶悍,不知何时会暴起打人,最好敬而远之。
两人一文一武,虽然同样跟随皇子,彼此却不怎么招呼。之所以变熟,是因为一个没其他人知道的契机──两人偕手偷了一只鸡,还在关公面前烧来吃了。
裴君玉一本正经的运用谋略打探,找出附近最肥的人家里最肥的鸡,故意把人引走。楚云飞则趁机溜了进去,当时他还不大会翻墙,差点发出声响──毕竟楚家的武功太过光伟正。
两人都家训甚严,第一次干这种坏事,各自都有些心虚。
但家训不能当肉吃。当叫化鸡烧好,两人七手八脚将泥土扒开,强烈香气随热气蒸腾而出,两人真心觉得,家训什么的,就从自己这一代改吧。
接着,在吃鸡途中七嘴八舌的闲聊,才发现──这家伙看着也挺顺眼嘛?!
谁也不知道,名满天下的大将军和裴军师,让敌军闻风丧胆的组合,第一次
的合作,居然是偷鸡。
楚云飞想到当年,忍不住笑:“想得很。可现在没鸡,你是要把我烤了?”
裴君玉也笑:“不烤你,烤我。”
这一刻,楚云飞隐隐觉得不对劲。
但眼前的人神色自如。“云飞,能不能帮我出去看看,哪家的鸡最肥?”
这是要楚云飞找能潜入的宅子。在这种状况下,再正常不过。
楚云飞犹疑半秒,问道:“君玉,你……”
裴君玉笑着打断他:“快饿死啦,你不去,我去也行。”
说着作势要起身。楚云飞按住他,同时也压下胸中闪过的不安。
他想,或许是自己多心,毕竟今日事故实在太多。而且,对方可是裴君玉,那个指挥若定的人。
楚云飞相信对方。
所以,他玩笑了几句,便闪身出门。
后来他无数次后悔这件事。
半个时辰后,楚云飞抱着热呼的馒头回来,这是他昧着良心从某户人家偷来的,老母亲热给儿子的宵夜。
楚云飞依照两人的习惯,在远处先扔了块小石头,没人应答。
以前几乎没这样过。
他猛然醒悟,踉跄着奔入庙中,那里只剩下一滩血迹,没有任何人影。
他疯狂翻找,企图找出蛛丝马迹,但什么都没有。
最后,他突然想到临走前裴君玉说的话。
──云飞,你还想吃当年的叫化鸡吗?
当时,他们两人在与今日类似的小破庙中挖了个坑,偷偷烧叫化鸡。位置在神坛之前,美名曰“请关公一起吃”。
每次提到都会大笑的事,此刻楚云飞却完全笑不出来。他急忙跪在神坛前挖掘,果不其然,下面有一块布。
是裴君玉的衣袖。
上面用灰简单写着之后让楚云飞做的事,清晰明了。看着这块布,楚云飞终于明白,对方早料到一切。
也料到自己的消失,或……死亡。
整张布上的指示清晰而不带情感,只有末尾缀了句玩笑似的话:“我的断袖可珍贵了,记得收好。”
10-行刑之刃(1)
深夜,楚云飞一个人靠坐在破败的墙边,脸埋在双掌中,久久不动。
漫长的夜晚没有过去,外面又湿又冷,笼罩在雨雾之下,一片灰蒙。
裴君玉最后留下的信说,他怀疑目前那批人背后的,是皇权及殷家。
他们被称为“行刑人”。一个古老的称呼,只出现在乡野逸闻中。
楚云飞知道他们,在家族覆灭后,他从废墟中残破的信件和笔记,一点一点拼凑起概略的形状。
开国之时,太祖和殷家的先祖,将狂热的追随者们,暗中组织成一个超乎常人想象的部队,被称为“行刑人”。
开国后,这些人受命隐匿起来,分散在各地,看起来就像是普通人。他们可能是乞丐,贩夫走卒,富商。看起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人生,但实际上,一切都在“那一位”的棋局之中。
组织要行刑人在什么位置,他们就会站在那个位置,扮演需要的角色。
他们是国家的影子,朱国的天罗地网。
太祖建造了一个光荣的时代,神话的时代。一切看起来欣欣向荣,但背后支撑着的,是暗影。
所以很快的,太祖过世后,便陷入一个泡沫般的年代,看似绚烂,实则是非黑白颠倒的时代。
在美丽的皇城中,出现许多肮脏黑暗的巷弄,出现两眼无神、因生活而麻木的人民。
还有,以谩骂为荣,以相残为正义的人。他们中的许多人衣着破旧,但因为侮辱他人,而觉得自己彷若王的使者。
在那个时代,人们普遍认为,一味偏爱、盲从自己的国家,才是真正的“爱”。愚忠于唯一的君王,才是真正的“忠”。
说自己国家有任何缺点的人,都是无礼之徒。皇城的命令是绝对的。其他国家之所以抵抗他们,是因为他们不识相。
因为国家是如此的繁荣和光明,所以不应有任何肮脏破败。穷人之所以贫穷,是因为不够努力或愚蠢,不值得同情,即使他们可能是因为天灾而失去家园和挚爱。
为国家牺牲,是理所当然,并且光荣的事。如果母亲因孩子在战场死去而哀哭,她会被丢石头。
这是以偏爱、愚忠为荣,以理性、客观、中正为耻的年代。它贯串这个王朝,如同黑色的母亲河。或许,它停止流淌的那一天,便是王朝终结之时。
现在,回到楚家的覆灭。
楚云飞的父亲,是个正直的人。
在历史上,广袤的世界上,他将被称为正直的人。
但很遗憾的,对于行刑人来说,他不是。
楚家忠于职守。但他们有自己的正义,而非以国家的正义为正义。
这就是一切的缘由。
年幼的楚云飞,独自在破屋中,一手握着生锈的铁戈,一手翻开
血迹斑斑的家训时,深刻的明白了这一点。
楚家覆亡的那天早上,没有人知道即将发生的事,一切看起来都很好。
小小的楚云飞还不习惯早起,洗了脸还是睡眼迷蒙,迈着短腿去和父母请安。
那天父亲穿戴得特别齐整,看起来精神焕发。平日沉默寡言的他,微笑着将楚云飞抱起:“家训背了不?”
小男孩脸上婴儿肥未退,还是喜欢父母抱的年纪。高高兴兴点头:“背啦!”
楚将军:“昨日背了哪些?”
突然被抽考小男孩有点嗑巴:“世人谓忠孝仁义者,多能言之,不能行之……礼缘人情,恩由义断……”
说到后面,小男孩停了下来,紧张的看着父亲。
父亲不笑了,脸色变得沉重。
怎么了?
楚将军喃喃道:“恩由义断……是这个理。”
恩由义断,用大义割断私恩,秉公行事,不徇私情。
他今日上朝要拿出的证据,足以翻一件陈年老案,或许会挑战先皇的崇高形像。先皇对他有恩,但他不后悔这个选择。
他忠于国家,忠于民。
他放下孩子,蹲低平视楚云飞,认真道:“云飞,你要记得这些话。”
楚云飞懵懵懂懂,但认真点头。
楚将军笑了,他走出门时,步履飒爽,看起来对未来充满希望。
接着,就是刀光剑影,血色的世界。
楚云飞被藏在暗格中,成为楚家的最后一人。
记得“恩由义断”的,只剩他了。
随着年纪渐长,他逐渐了解到,那一天发生了什么,高高在上的上位者,是如何利用背后的暗影,某些人的狂信,以虚假的正义姿态,践踏他的家族。
所以他选择反抗。
当听说一位皇子,因类似的理由而被迫出逃时,他知道,机会来了。
他效忠这位皇子,最终和同伴一起,昂首挺胸的踏入京城。他们看起来很成功,前朝造成的混乱逐渐恢复秩序,新的皇帝和“行刑人”关系淡薄,似乎也不屑利用他们,对国家有着鸿图大志。
可是,他们没有想到,费尽全力推倒一座邪恶的神像,并不是终结。
或许,仅是另一个恐怖循环的开始。
11-行刑之刃(2)
当时的楚云飞,并没有认清这一点。
他觉得时机已足,为了引出蛰伏的行刑人,他刻意报复,行止几近疯狂。
最广为人知的,是他将构陷他父亲的权贵,已死去的、楚家表面上的仇人,挖坟鞭尸。
他将对方的坟挖开,对着半腐发臭的尸体挥鞭。一声声沉闷的鞭响,让他胸口发疼,最后再也承受不住,差点跪倒在地。
但他强忍着站直,装成大仇得报的模样,扔下沾满血肉的鞭子,径直回府。
回去之后,他整夜没睡。
现在回想,做这件事时,不只毁坏了对方,也弄脏了自己。
但当时的他,一点都不在乎。
全都毁灭也没关系,被火燃烧殆尽也没关系。
裴君玉尽力阻止过他,他没有听。
没多久,裴君玉自求远离京城。以他的功劳,明明可以取得很好的封赏。
他上奏时,众人侧目。有人以为这是欲擒故纵,想让皇上封赏更多的把戏,但裴君玉是认真的。
楚云飞静静看着。当时的他也觉得,裴君玉远离混乱的京城较好。
皇上从一开始的不敢置信,到最后露出疲惫的表情,批准裴君玉的请愿。
裴君玉离京的那天,楚云飞策马送行。两人都没说什么,只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,便俱都沉默--当时的他们,已经很难多说什么。
分别前,裴君玉只是悲伤的微笑。“保重。”
楚云飞没什么表情的点头。他没将这句话放在心上,只当是一句普通的饯别语。
对他来说,引出行刑人,把暗影拔除,远比他的生命更重要,更何况“保重”呢。
为了达成目的,他愿意弄脏自己,或者,成为比行刑人更尖锐的利刃。
最终,他死在烈火之中。他以为行刑人的掌权者是姬家,但他猜错了。行刑人依然在幕后活跃,一切没有任何改变。
现在回想,楚云飞突然觉得,那是被执拗扭曲的他,应得的结局。
世间最可怕的事,不是面对无法战胜的敌人,而是想打败敌人,自己却被同化,变成和敌人同样丑恶的东西,落入深渊中。
这是最彻底而可悲的失败。
所以,发现自己活过来时,楚云飞已决定放弃。
毕竟,属于楚云飞的身体已经消失,楚家的血肉还诸天地,他似乎是一个新的生命。
但事实并不是如此,简直像老天开的玩笑,他又做为“楚云飞”回到这个世界。
究竟这件事的意义何在?沙民认为这是神迹,但楚云飞厌恶信仰。
无论是行刑人之于国家,靖王之于藩民,还是他自己之于沙民。
神像能被打倒,但信众不会被打倒。他们像铺天盖地的雨,像连绵春草,成群的出现在这个世界上,建造新的神像。
一切只是重复的循环。
承认这件事,对楚云飞而言非常困难。可他不得不承认这点。
他蜷缩在墙边,像幼年刚家破人亡时,躲在夹缝中。他恨无能为力的自己,所以幼小的他拼命锻炼,希望快点长大,打倒敌人。
但长大了才发现,面对这个世界,自己还是像幼童一般无能为力。
掌控这个世界的,到底是什么?
他茫然的握拳,又松开。外面的雨簌簌下着,一切似乎没有尽头。
但此时,脚步声响起。雨啪啪落在伞面上,有人行近这间破屋。
楚云飞没有动,裴君玉的指示很明确,但他已经不想动了,至少此时此刻。
最后,玉白的手轻覆在他流血的拳上。
墨黑的发垂下,略为憔悴的秀丽面容,如同被雨打湿的白山茶。